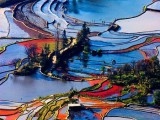于建嵘法学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底层立场》等。
早报记者罗晟
2011年新年伊始,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的行程排得很紧。除了受邀在各地方给党政机关人员讲课,他还在组织一个青年学者培训班。
1月中旬,哈佛燕京学社、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三个学术单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协助下,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二期有关中国民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培训班。
“理解中国当前的巨变及走向,必须理解底层社会。我们需要为中国转型作好理论准备,本培训项目致力于培养青年学者,去研究底层社会。”于建嵘介绍说。
来自内地和香港地区的20名学员参加了为期10天的培训班,从中将选拔3-5位学员前往哈佛燕京学社进修一年。
于建嵘希望在国内外学术机构的支持下,让培训项目能够坚持五期,即从2010年至2014年。“5年之后,我们不期望培养的100个学员都留在这个领域,但是哪怕留下20个人,可能10年以后,就有顶尖学者在发言时谈中国的底层社会问题。”
于建嵘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单位平均主义制的社会结构。社会不平等加剧,社会结构分层日趋明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中外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是中国的底层社会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中国。此次培训项目致力于纠这个偏差,集中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发展方面,深入考察中国底层人群生活的细节和事件。
在结课时,于建嵘对学员们说:“无论能不能到哈佛去,希望你们能够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的底层社会。这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未来学术走向的一个重要判断:关注底层社会的诉求和行动,对中国未来社会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的缺失,可能对中国将来社会转型,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县级政府是主要拆村动力
“以前拆村主要是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去年我最纠结的地方是,拆到了边远的农村。”
东方早报:当前在农村征地、农民工二代、环境问题等诸多社会热议方面,你认为哪个是当前农村最核心的问题?
于建嵘:农村的环境问题和农民工二代问题都很重要,但主要问题是拆村问题。当前农村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拆村运动带来的土地问题。
2010年为什么我们这么焦虑,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发生了一个拆村运动。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抢夺农民土地的事件。
这是中国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去拆农民的房子?为什么拆农民房子引起了这么大的民怨?以前拆村主要是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去年我最纠结的地方是,拆到了边远的农村。
东方早报:拆村与一般的土地整治有何不同?
于建嵘:农村拆迁和城市的拆迁有些区别。因为城市的拆迁是项目制,即开发商是当事人。而拆村的情况则是,政府就是当事人,政府要去组织拆村,让农民上楼,上楼之后的宅基地指标被拿到城市周边去进行土地交易。
拆村主要是指在增减挂钩中间,对农民宅基地的侵犯。这和一般的拆迁是不一样的,已经牵涉到农民的宅基地了。
增减挂钩的主要问题就在这一过程中间,地方政府可以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去搞农民的土地,但如何保证农民的自愿,是没有具体政策的。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很多办法,可以迫使农民答应离开土地。这个自愿性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拆村来自于没有大型建设项目的地方。有大型建设项目的地方,国家会给地方建设用地指标。拆村运动最大问题在于因为不存在这种大型项目,地方政府为了得到用地指标,通过增减挂钩的政策来操作,想利用拆村来获得用地指标。这种用地指标不是为了大型项目,而是为了本地即县级政府,县级政府是主要的拆村动力。{Npage}
陕西老农民的智慧
“我并不认为有些村庄不能撤,但是那是人家家里的东西,有些事情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
东方早报:怎么看待征地过程中的补偿价格问题?
于建嵘:农民土地溢价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价格更复杂的是,拆村影响了民众的基本生活生产的问题。
拆村遇到的价格问题,和一般的城里拆迁中位置和价格的问题不同。因为拆村的后果就是农民将来的生活和生产的成本要增加,比如现在住在农村,农民的煤气费、物业费是没有的。但是一拆村之后,我就必须要上楼了,要交物业管理费。生产成本也在增加,体现在要去很远的地方才能种田。这些生活与生产的问题使村民反抗,并不完全是个价格问题。
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不管用什么价格,最后到农民手中的并不多。而且所有的价格要有自愿原则,现在的拆村运动可以破坏这种自愿原则,这是最大的问题。
拆村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用地指标,不只是村庄的用地指标,不是农民的问题。农民为什么不自愿?现在是必须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价格?自愿的问题不解决,谈价格是无本之源。强迫农民卖地怎么办?不平等怎么谈价格?而且钱不是落到农民手里去了。有的人认为拆村好,农民可以卖地了,但是人家不想卖,你让人家必须卖。
我在陕西做调查的时候,碰到一个农民特别有智慧。政府跟一个农民谈:“你看看,你现在这一亩地,一年种玉米就只有300多元收入。我现在给你3万块钱,是你100年的收入。”老农民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实话,现在种玉米一年是300多块钱,但是你给我3万块,放在银行里,没有地了,两年就吃完了不?假如现在地在这,哪怕一年只产300块钱的玉米,我子子孙孙都有个生活,还不讲将来会怎样。”
你看农民的思维和官员的思维并不一样,存在两种对未来生活的判断。理解这种区别很重要。
我并不认为有些村庄不能撤,但是那是人家家里的东西,有些事情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比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们两个兄弟商量下,把你的东西卖了,这怎么行?有些东西不是通过表决能够决定的。
应用个人的权利意识来支配我们的思考。我反复讲一个观念,一个县委书记做了一千件好事,但是你做了一件坏事,破坏了社会规则,这就不是好官,不是好人。不要告诉我为了农民做了多少好事,为社会建了多少高楼,但是你只要剥夺了人家的权利,破坏了社会基本规则,就是不行。我们需要一种对社会规则的基本理解和认同。
老年农村妇女走到前台
“从控告方面而言,村民联名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村级组织也在成为重要的控告方。”
东方早报:如何看待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
于建嵘:从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关于三农问题的分类统计中可以看到,2004年前,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是抗税抗费,2004年后,农民主要维护土地权益。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第一焦点问题。
农民土地抗争的当事主体发生了变化。目前就农村土地纠纷之较税费争议来说,在双方当事人方面有着较大的变化:从控告方面而言,村民联名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村级组织也在成为重要的控告方。
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村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老年妇女走到前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从土地纠纷的被告方面来说,市、县政府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政府很少成为被告的主体。特别是,在目前的土地纠纷中,一些房地产经营公司和开发区成为了被告方,这在税费争议中是没有过的。
农村土地抗争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者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两级组织。
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变得相对激烈。在农民抗税维权时,由于中央有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动用警察处理纠纷时要承担政策和农民反抗的双重风险,所以除个别事件,很少在税费问题上发生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而目前的土地维权抗争活动中,由于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动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
农民土地抗争的外力介入情况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精英的介入,有许多事件就会离开土地纠纷本身而成为政治事件。而开发商甚至地方政府有时也借助黑社会性质组织压制民众。
维权事件的四个基本特征“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
东方早报:如何看待农民的土地维权行为?
于建嵘:包括农民、工人和市民在内的维权性事件有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利益之争而非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
这些维权事件都是因经济问题而引起的,如拖欠工资和补偿款等,维权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虽然在有些维权事件中成立了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协调机构,但其最终目的不涉及任何政治目的,而只涉及具体的经济问题。他们虽然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和目标,但都针对具体问题,在其行动过程中,他们是尽量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活动的。一旦他们拿回自己的工资和补偿款,他们就会满足而自行解散。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如何对待和解决维权事件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这些事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通俗一点讲,就是用人民币就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决定了这些事件虽然会给地方政府造成一些麻烦,但由于他们的愿望比较容易达成,因而又较容易解决。
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的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
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来进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比如政府的许诺而不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
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同时,公民的权利意识大为增强,他们意识到其应当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为此必须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使他们在具体行动中能够理直气壮,并认为自己拿到侵权方的把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怕”。
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具有明显的被动性。
目前中国的维权行动,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因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通俗地说,只要你不找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就不会主动找茬,他们只有在自己受到侵害时,才会找政府的麻烦。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
但是,某些事件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甚至会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引发恶性暴力事件,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目标是合法的,也是受到法律支持的。但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他们不可能全部通过法律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更多的是寻求法外渠道。因而他们的行为中有一些是非法的,比如破坏了设施,打了警察,砸了汽车。
从目标与手段关系而言,各主要维权事件的目标均具有比较高的合法性,而部分维权者获取目标的手段,则可能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如虽然上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在上访过程中,他们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围追堵截,甚至强制关押。
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宪法是稳定社会的底线。面对当前的社会冲突,全社会需要的是理智,执政者需要的是智慧,研究者需要的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