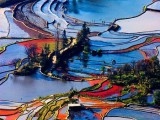一、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丧失了村集体对土地的权利,村集体就会成为一个空壳,村民自治就缺少了经济基础。道理很简单,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合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所有权主体是村社集体,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主体是农户家庭。村集体最主要的依据是其作为村社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及在这一地位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各种关系。村一级虽然是一个行政层级,但并非基层政权,而是一个社会性组织。离开了对土地的权利,村集体既无固定收入来源,又无行政权力,村一级就纯粹成为一个上传下达的层次,而难以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也难以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也就成为空谈。
党国英认为,村一级就是不应该有权利,村干部权力越小越好,因为他们权力越小,就越发干不成坏事。问题是,一旦村干部权力小到什么坏事也干不成时,村干部也没有干成好事的能力了。村干部权力越小越好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国家行政性权力退出农村基层,农村社会秩序由农村内生的秩序性力量来维系。村干部无论好事坏事都干不成,村级选举就不会有人感兴趣,也不会有人愿意参加村委会选举。作为一级社会性组织,村集体的主要权利来源是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之所以村一级仍然重要,是因为在村庄这样一个局促的地理空间上,生活着上千口人,上千口人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出各种生活的、生产的公共事务,就需要有解决这些公共事务能力的人或机构出来主持维持。
近代以来,在国家不断从农村汲取资源,农村社会发生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面,农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人财物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农村越来越处在失血状态,这个时候,农村获取秩序的资源基础十分薄弱。但另一方面,生活在村庄这个局促空间的村民,仍然有着众多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公共事务,需要有人或组织出面解决。这个必须出面解决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就不能只是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而必须是有一定行政权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组织,这个组织,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村级组织,或村社组织。村社组织具有双重身份,一是村民自治组织,二是村社合作经济组织,村社合作经济组织的核心是其作为村社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作为村社土地的所有者,村社组织将土地承包到农户家庭经营,农户向村社组织交纳一定费用(“三提”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村社组织用农户缴纳的费用来建设村社公共事务。正是有了农户缴纳的“三提”,村社组织才有了可以运作的经费,才有了可以办事的经济能力。
村社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向农户提取“三提”经费,是与改革开放后农民负担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农业税收,二是乡镇五项统筹,三是村级三项提留(“三提”),在实际的农民负担管理中,三项完全不同的农民负担往往绑在一起。到了1990年代,全国各地农村又向农民收取名目繁多的集资,最终,农民负担恶性膨胀,农民越来越不愿缴纳税费,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向农民收费,干群关系严重恶化。中央越来越感到,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太高,而获益甚少,加上国家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国家终于在2003年开始取消农民负担的税费,包括农民所缴纳村社集体的“三项提留”。
一旦取消三项提留,村社集体与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古怪,因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不再需要对集体承担任何义务,村社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就变得可疑。更重要的是,村社集体再来办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就难以利用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所可以发挥的筹集资源的作用。这恐怕就是李昌平所说,村民自治因此丧失了经济基础的意思。
即使不再允许村社集体向承包土地农户收取“三项提留”,若允许村社集体调整农民的土地,村社集体或许还是有办法来获取一些进行公益事业建设的费用。比如,村社集体可以通过调整土地,来预留部分机动地,再将机动地承包出去,收取一定的承包费,用承包费再做成一些事情。2004年在陕西武功县新庄村调查,全村各村民组的治理状况与村民组机动地的多少有着极其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即机动地越多的村民组,组内公共品供给越完善,组长工作积极性越高,组内村民越团结。而没有机动地的村民小组,没有人愿意干组长,组内公共事务无人管,组内人心涣散。2007年在河南扶沟县调查,一个村因为有200多亩集体的林地(已经改种庄稼)没有承包出去,村集体每年通过将集体林地承包出去所获收益,来举办村集体的公共事业,也很快办出了些事情,村民满意,村干部也有长远规划。
即使村集体不通过调整土地为集体留下机动地来获取集体收益,调整土地也有助于村庄公共品供给。典型如2007年在河南汝南县宋庄村调查的情况。宋庄发展蔬菜种植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村庄内的道路状况很差,进村运蔬菜的车辆难以通行,修建水泥道路,对宋庄村民来讲,是关系到他们生产能否正常进行的十分基础和重要的公共品。正好国家有修建通村道路的资金支持计划,再加上县乡两级的资金扶持,宋庄村找到了修路的经费。但修路要占地,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地被占,若修路占地后,村集体不调整土地,占地农民就一定会要占地补偿。宋庄村修路一共要占地10多亩,按每亩补偿2万元,村集体就得拿出30万元补偿占地村民。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当然也就无法补偿村民,国家扶持修路的计划因此就无法进行,农民的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因此得不到改善。最后,宋庄村干部决定调整全村土地,也就是说,占地农民即使自己的承包地被占了,也可以在来年的土地调整中,按人口来重新匀分修路占地以外的所有耕地,修路占地的损失由全体村民来平均承担,其好处也由全体村民来享受了。
土地是村社集体的,调整土地也一直是村社集体可以行使的权力。中央之前规定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只是讲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村庄集体,农户有权承包集体的土地。中央政策精神是基本制度不变,就是以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制度不变,但具体承包关系则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村社集体可以根据集体用地的情况,可以根据农户人口的增减,每隔几年调整一次土地。而在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15年不变”到期后的1990年代中期的各地政策实践,是依托中央在1997年11号文件规定的是延包30年不变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延包并非一定要延续第一轮的具体承包关系,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是依据农户人口增减进行了重新分地。这个意义上,30年以后,第二轮延包结束之后,农村应该依据当时的人口增减,再来进行新的土地分配。糟糕的是,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逐步将基本经营制度的长期不变,变成了具体承包关系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不变”变成具体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再变,这样就搞成了一个架空集体所有权的“永佃制”来。村社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利因此丧失了,通过调整土地来获取村社收益,来分摊公共事业费用的空间也被堵死了。
也就是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社集体,现在不仅无权向承包土地的农户收取任何费用,而且不能通过土地调整来行使权利,农户在土地上的利益结构被固化,村社集体被彻底架空。目前国家安排给村社集体解决公共品供给的制度是“一事一议”,即村社集体可以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每年向每个人收取不超过15元的费用,用于村庄公共事业的建设。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是,若有人不愿意交钱,村社集体毫无办法。而只要有一个人不愿交钱,就会有更多人不愿交钱,最后,这样一个几乎是毫无强制力的制度就在实践中流产。目前全国农村,仍能通过“一事一议”筹措村庄公共事业建设费用的,可能十不过一、二。
离开土地收益,离开一事一议筹资渠道,村庄内可能用于公共事业建设的费用,就只剩下两条,一条是向村庄在外工作的人募捐,这显然不可能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形式。另外一条就是指望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已经很有钱的背景下,这条倒是很有可能。但目前中央似乎也不相信村一级,甚至不相信乡镇一级。中央通过两条途径向农村进行转移支付,一是直补到户,这样,任何中间环节都不可能克扣。另外一条就是通过条条,现在搞得条条权力极大,条条专政,而块块只能“跑部钱进”了。
看来,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中央不相信村干部。中央认为,村干部只要有了权力,就会滥用权力,就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党国英因此总结说“村干部权力要小”。但是,离开村干部,村一级的公共品供给断难有改善的希望。我曾在过去的文章中论证,在自上而下的汲取型体制下面,强大的压力型体制,使乡村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可以架空村民自治,使村委会选举流于形式。在农业税费取消,压力型体制大为松动的情况下,乡村利益共同体已经解体,这个时候,正是可以发挥村民自治,可以让农民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时候,国家偏又将村级组织的所有可能的功能取消。一旦村级组织不再有功能,村干部不再有权利,即使有真正的民主,又有何用? {Npage}
一句话,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办法,一是要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要完善村民自治,要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充分条件,一是要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要给村干部以可以办得成事的权力。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村社集体的实力,则中央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给村社集体一定的实力。当前中央政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且我以为,从农村公共品供给,从农民对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获取角度来看,中央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未必明智。
二、村庄、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一、中国是有农村的,而美国只有农业。在美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少则数百公顷,多则上万公顷的家庭农场,这些农场主的生活是城镇生活体系的一部分,基本上不存在单独的村庄生活。美国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主所经营农地的面积,与中国一个普通村庄耕地面积相差不多。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人口在1—2000之间,耕地面积2—3000亩,农民人均耕地在1—2亩之间,人均2亩多地,就是土地多的粮食主产区了,很多地区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亩。
在如此局促空间居住如此之多的人口,且农村主要农地只能用于生产大宗农产品尤其是水稻、小麦、玉米,中国农村就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的土地制度也就有其独特之处,且因此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也有其独特之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以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就是说,在村庄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集体,但村社集体的土地必须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方式是按人口均分,每个人一份地。为了公平,分配承包地时,肥瘦搭配,一户分了10亩地,往往分布在村东村西不同的方向,共有十几块。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农业人口密集住在村庄从事农业劳作,村庄是人们的归属,乡土深入农民的血脉。村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场所,是他们的根,是生命意义之所在。村庄又是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在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乡土社会中,长成了一种有效处理密集相处人群关系的规矩,正是这个内生规矩,使广大的乡土社会在常规时期无需自上而下的权力介入,就能有序运作。中央政府对广大农村采取“无为而治”的治理策略。村庄是一个共同体,既有规矩,又有村民的认同,既生产粮食,又生产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外生型现代化,要求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国家通过政权建设,逐步建立起伸向农村的密集管道,从农村抽取资源,农村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秩序被打破,村庄作为共同体越来越难以维系。新中国成立后,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进一步强有力地渗透到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完全重建了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以前主要依靠内生力量维系的乡村秩序,现在已被人民公社的严密组织所取代。人民公社不仅有效地从农村提取了大量用于现代化建设的资源,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内部的生产结构和生活状况,其中的一个后果即是通过多年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建成一整套与集体经营相配套的水利基础设施,并一举将中国可灌溉耕地由建国初的18%提高到46%,这46%的可灌溉耕地生产了中国70%以上的粮食。
二、
分田到户以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试图在保持集体(统)合作能力的前提下,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这样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分田到户不仅调动了农户个体积极性,而且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有效地利用了统的力量,比如乡村组织通过提取“共同生产费”,为农户提供生产的基础性条件。正是因为有集体组织的统的力量起作用,千家万户的小农仍然可以与人民公社时期建设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接。
村社集体组织不仅在为农户提供与大中型水利设施的灌溉对接上作用极大,而且,村社集体还是农户与市场,农户与国家对接所不可或缺的中介。国家有时也利用村社组织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通过村社组织向农户征收税费。国家通过村社组织向农民征收税费,在1990年代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中一项严重后果就是农村干群关系对立,村社组织不再被农民信任。国家还利用村社组织来完成其他的国家任务,其中最不受欢迎的另外一项国家任务是计划生育。在1990年代,乡村干部包括村社干部的主要任务被概括为“收粮派款、刮宫引产”。离开了村社干部,县乡两级即使要进村找人,也很难找到。
村社组织显然不只是在协助国家做对农民不利的(至少是不受农民欢迎的)事情。离开村社组织,国家想在农村做好事,恐怕也会十分地困难。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社干部天天与村民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极为熟悉,各自也无秘密可言。这种建立在邻里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熟悉,及因之而来的信任,是国家力量渗入到农村社会的最好凭借。中央的好政策,仅仅电视和广播宣传一下,还是太遥远而不可信,村社干部现身说法的效果完全不周。湖北建始县的一个村支书说,无论中央的惠农政策如何难懂,只要他能领会,他就有办法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让村民代表领会,领会了中央精神的村民代表有的是与村民接触的时间,也就有的是让村民领会中央精神的办法。
除了宣传中央政策,自上而下的各种农业技术推广,上级只有在村里找到了有力的协助者来办点,这个技术才容易在全村范围迅速地推展开。过去农技推广中有办点的经验,办点的前提是有村社组织的支持和参与,离开村社组织,县乡的技术部门就悬浮在空中,推广农业技术就成为空谈。刘岳曾说,仅仅加强乡镇农技部门的建设,而忽视了村社基层组织建设,忽视了村社组织这个中介,农技推广就难以取得成就。不只是农技推广需要有村社组织作为中介,来实现与小农家庭的对接,甚至防治禽流感,离开了强有力的村社组织,国家也很难有办法及时掌握动态,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离开村社组织,任何提供给农民的服务都要打折扣。
农民也需要通过村社组织来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当今世界越来越流动,也越来越复杂。村民外出务工,遇到工伤事故,他无力应对,也不懂得应对,他最常求助也最可以求助的就是村社组织,及以村社组织为基础建立起联系的自己家乡的县乡政府。农民外出务工,他在家乡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出现意外,他也要指望村社组织。村社组织越来越成为农民应对危难的可能找到的求助对象。
简单地说,在中国农村,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人均1—2亩耕地的小农的规模太小,从农民与市场和国家对接的角度看,村社是最小的单位,正是村社这个中介,为农民联系国家,联系市场,提供了相当有力的基础,村社因此成为一个最小的公共品提供单位,成为一个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条件的单位,也成为一个国家管理和服务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而村社之所以可以具有如此之重要功能的一个基础条件是,村社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农民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农民可以最后求助的底线单位。
三、
不过,当前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即,在中国农民并非真正转移进入城市社会,农民还需要依托村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时候,村社熟人共同体却在迅速地解体。导致村社解体,有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一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外流,而城市理念进村,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资源外流又使村庄维系内生秩序的能力降低。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必然过程。另外一种力量则是与政策有关。比如,当前中央越来越倾向将之前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承包制度的稳定转变为具体承包关系的稳定,甚至变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长久不变的土地承包关系,村社集体对土地所有的权力被架空了,而农户则“永佃”了村集体的土地。农村“永佃”集体土地,但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庄进入城市,并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世界,都已经到了城市,但他们的土地仍然在农村,他们仍然占有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将土地出租而收取地租,而租地种的农民大都是无力离开农村而进城安居的村民,农村资源通过地租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城市。更糟糕的是,这些已经在城市安居的原村民,他们已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渠道,他们并不关心土地的收入,他们也不会(没必要)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廉价买掉(农地的价格肯定不可能高),他们并不认真对待土地,而是将土地占有在那里。
在村庄中,不依靠土地生存但却占有着土地的城里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村庄的内聚力就会成为问题。而若建立在“永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一旦开始形成规模,则脱离村社成员权的土地占有关系也会变得普遍起来:因为土地是被当作生产资料来流转的,一些占有土地的人却不具有村社成员资格,通过土地流转进村经营农地的外来者(公司或个人)也不需要村社成员资格,则村庄共同体的维系就更加困难。本来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村社组织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复杂的经营着村社土地的人员结构中,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来继续充当村社小农与外部市场及国家关系的中介:即使这个时候村社因为被国家重视起来,而具备这个能力。
在农地收益很少的情况下,土地应该是真正需要耕种土地的农民的土地。在大部分农民仍然需要依托村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下,村庄应该是真正需要依托村庄的农民的村庄。当前的问题是,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破坏以上两个“应该”的自发力量,而且国家似乎对此“应该”缺少敏感,且事实上正在通过政策破坏以上两个“应该”。